|
|
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没有学过音乐的人能有机会与那些头顶耀眼光环、为无数人所尊敬的音乐名家接近,而且是如此近距离地走进他们的生活,采访并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共同谈论社会和艺术话题。自1999年我进入《音乐周报》这一专业媒体以来,在一次次的采访中,这些音乐家向我和读者展露出最真实的诉求,一如身边的普通人。而他们的情感和经历不断影响丰富着我的思想,使我更细腻地感受生活,感悟人生,也使《音乐周报》的版面常常感动和感染读者。 * m3 M. ?. f) e( H' c; p, d5 Z1 k
4 f2 W& t+ ] I$ h% P
像老朋友一样亲切 ( K4 q: N1 S' ~$ b
; D; P- f$ y9 y9 C 我进入报社采访的第一个人物是著名作曲家傅庚辰。那是在11月,刚刚结束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代表大会上,傅庚辰当选新一届中国音协主席。报社得到消息,立刻派我做专访,准备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说实话,我当时对音乐界很不了解,该怎样对话呢?我赶紧找到老总,他告诉我中国音协主席已经空缺了十年,人选确定过程很艰难。于是我想到傅庚辰本人心情一定也很不寻常,第一个问题就从他的心情谈起了。看得出来,傅庚辰平静的外表下有一种难掩的激动,听了我的问题,他似乎没想到我会问得这么直接,顿了一两秒钟。我赶紧说:“我想很多人都很关心您的心情呢。”这句大实话让傅庚辰彻底放松了,笑着说:“我的心情很平静”。随后又谈了些以后的想法。傅庚辰是军队艺术家,非常严谨细致,盛名之下令许多人不敢接近。后来他告诉我,正是我的直率、明朗的态度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把他还原成一个普通人。 2 {' r* T* E/ i9 v1 X
6 r, M# E) Y* {; R# ]8 l
后来,随着对傅庚辰采访的增多,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个表面威严、内心细腻的音乐家。在每篇报道中,我都会从全局把握,客观真实地反映音乐界的情况。傅庚辰是我们的老读者,多次看过我的文章后打电话来交流。在许多场合见到我时,他总会对身边的人笑着介绍我:“我们是老朋友了。”在他的建议下,我参加过中国音协不对记者开放的内部工作会议,还亲眼目睹他为中国音乐最高奖项金钟奖的设立上下周旋、费尽思量,了解到许多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 M9 r) i, ~! n7 y# s
. C5 K1 ?4 g! h' N/ O" ? 叫一声老师最开心
& v0 h6 H( ^/ a; N% Z
4 k. q2 ?) ~+ d3 v8 ^0 h! k 第一次采访金铁霖,是在2001年。他培养出彭丽媛、宋祖英、张也等歌唱家,担任着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是音乐界的重量级人物。当时,中国音乐学院开办的声乐硕士班第三届学生毕业。硕士班在声乐学习者中反响良好,然而由于一些现实问题必须停办。金铁霖的心情很复杂,想通过报纸对社会有个交待。没有正式接触前,我以为他一定是张扬的,架子很大,而且音乐圈对他还有一些议论。因此,当我去中国音乐学院采访他时,我想跟他也不会有太多共同语言。带着这种潜在的“不友好”,我走进了金铁霖那间看起来比较简朴的办公室。稍事等待,金铁霖迈着略显疲惫的步伐进来了,他看起来有点郁闷。随意地坐定后,他跟我马上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而一句也没有谈到他的功劳。言辞中透露出的对培养声乐人才的热情渐渐打动了我。我意识到,我面前的这个人不再是什么大人物,而只是一个为音乐事业殚精竭虑的声乐教师。我在文章中,把他的这种状态细腻地传达给了读者,金铁霖很认可,说我对他观察得很细。 # Y. x7 p5 ^8 _
* o+ z# u9 k* E, [1 J4 x
2004年,金铁霖当选北京市文联主席,成为这个职位上第一位音乐人出身的领导。我打去电话,但是听不出来他有什么兴奋的,谈了一些想法和自己的活动安排后,他突然冒出一句:“我其实最喜欢当老师。”很少有人会在这种时候说这样似乎不合时宜的话,但是我能体会到他是真心的,而且是信任我的。跟他的交往渐渐增多,无论是重大比赛还是节庆活动,对他的报道我都会首先把他作为一个教师来对待。而面对各色媒体的采访报道,他对《音乐周报》的声音非常重视,每次不管在外地出差,还是开会间隙,他都会抽空愉快地接受我的采访。一次在某个发布会上见面,寒暄几句,他凑近我,又是一句:“我还是喜欢上课的感觉。” # I; W5 F z4 Z* g2 u( Q
# p2 j6 n3 _5 l, q- Z: A5 _% R
鬼丫头一样的好“哥们儿”
# U4 I) e) D+ X( V
& Q. d5 r' J5 _6 G/ ^. ?# ]4 _ 唐俊乔是蜚声海内外的青年笛子演奏家。2002年,她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在电影《卧虎藏龙》音乐中担任笛子独奏,《卧虎藏龙》得了奥斯卡最佳配乐奖,一时间,欧洲观众对原版电影音乐和唐俊乔甚为追捧。唐俊乔很聪明,抓住时机,积极与中国作曲家合作,走上了一条与交响乐队合作演绎中国民乐现代作品之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声名大振。我是在2002年底认识唐俊乔的,我发现她很有想法,比一般的演奏家更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不是拘泥于音乐谈音乐,而是用前瞻的眼光考虑全局,也没有矫揉造作之气,而是有难得的学术气质。我很喜欢她的这股勇于创新、敢想敢干的劲儿,每次采访交谈,都会仔细聆听她的一个个创意,她的想法给我很多做报道、抓选题的灵感,她的热情也督促我写出更真实、更生动的文章。唐俊乔时常跟我说,她的想法得到我的鼓励,也增添她往前走的信心。可以说,是对音乐事业共同的负责精神,让我们俩成为无话不谈的“哥们儿”。她跟我同岁,聊起来多了一份随意,话题从事业也扩大到了生活,甚至会讨论结婚、生孩子这样琐碎的事情。
! S* i& Z2 Z; ~1 E. {. }8 W t4 l$ q: h! z6 A. F4 a* v
5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唐俊乔的发展,她不管走到哪里演出,都会给我“汇报”;我也会慎重选择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报道。我们彼此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也都会互相倾诉一番,她的事业越做越红火,我和她的亲昵和默契却一点儿没有变,这种关系的存在让彼此的生活多了一份不一样的色彩,这份温情也不断地温暖着我的采访生涯。 ; E& a6 h/ x* g6 F0 v" [; ?
' w) s$ z8 w' s. K: G
进入《音乐周报》以来,我认识了各色各样的音乐人,成为许多人可以说知心话的对象。这是我当记者之初所没有想到的。我想,能得到这些才华横溢的音乐家的认可,也许是因为我对音乐怀有一份神圣,因为没有音乐专业背景而少了许多小圈子的羁绊,还因为我对中国音乐生存大环境建设的那一份挥之不去的责任感。总之,真诚地对待音乐人,就和他们没有障碍,就像只有真诚地对待音乐,才能写出动人的旋律一样。▲
9 B, L6 A1 D O, w+ G m7 ?1 W3 l7 I% c U1 m
' n* p1 l4 Y( M/ ?, M' y
* M3 p" h" B1 A
/ c) k! }" j5 u1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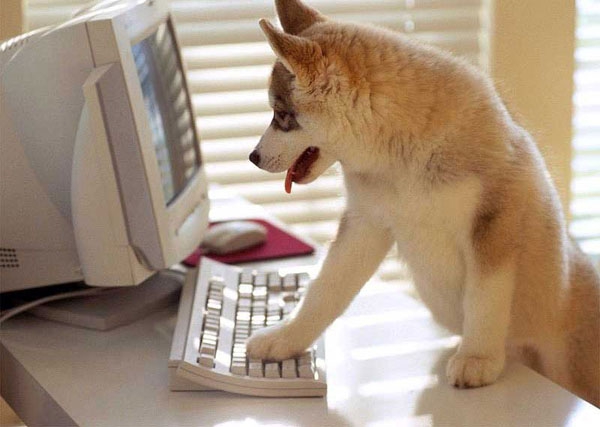
4 s+ ]0 _1 N. |( L3 k: H- {% t2 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