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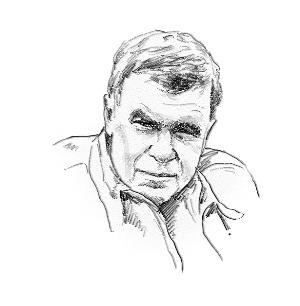 . K4 P9 s5 `# j: V. c( q
. K4 P9 s5 `# j: V. c( q
7 Q8 |3 _! a9 Z/ I% U2 |' H
雷蒙德·卡佛,“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2 P% Y+ P5 j; x: S8 X
- V' |+ K+ V. h/ D8 L- y! e 提起卡佛,中国文学爱好者不会感到陌生,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大教堂》《我打电话的地方》,堪称百读不厌的经典,正是这些不朽名著,在我们的脑海中塑造出这样一幅卡佛的形象:干脆、冰冷、酷、充满爱的残忍、直面现实的坚忍……7 c3 h5 d: p" A! n& }
( ~3 }$ D% Y2 w2 f
但,这很可能只是幻象。+ g+ @2 u: v2 Z9 q2 L9 d5 @
9 L. D& \/ o7 D2 g 因为,卡佛的小说曾经被出版编辑大幅改动,特别是他的成名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为满足美国中产阶级阅读品位,原作中温暖、舒缓、细腻的地方基本被阉割殆尽,仅突出了故事性和冷酷的一面。0 o1 L$ j) D, r" }) f& w
! ~* }! E* h% h4 y. Q& i9 e* M 换言之,卡佛并不“极简”,而是被“极简”,在赢得满堂喝彩同时,卡佛也失去了自身的写作特色。对此,卡佛一直耿耿于怀,生前曾多次希望能将原版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付梓,可惜直到身殁,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3 s/ _/ _6 Y4 H6 L( F
; i7 m g% a# B% j& L% X 今年,译林出版社将《新手》(即《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原版)译成中文,初读之下,令人愕然:那个干脆利落、冰冷决然的卡佛怎么突然变成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新手》在艺术上是否是一本失败之作?对此,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L" N. l' S0 Z) U9 j2 ^* q8 g) k: A( e. N G5 ^8 q
编辑创造了卡佛
, k1 h' Z) S5 I2 a5 I( e# h+ z" Z2 w6 s' [+ M
如果你让我现在投个票,说我是喜欢《新手》还是喜欢《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下简称《谈爱》),我当然喜欢《谈爱》,因为《谈爱》是我20多年前就读的,而且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正因为我如此的喜欢《谈爱》,我也有兴趣来读《新手》。5 z3 `4 f$ l, L0 a$ w
5 m/ ]7 V/ v* s) G3 `
比较两个卡佛,一个是在《新手》中没有被编辑过的卡佛,一个是在《谈爱》里被编辑过的卡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本人是编辑,在这件事上充分表明了编辑的伟大和编辑的罪孽。
" S# e/ l! w o# _' }7 Z3 D5 D; Z6 \/ _4 ^" ] s5 ~; _3 `
可以想象,当年卡佛那样一个文学青年,走投无路,写稿子没人发,忽然有个大编辑对他垂青,而且确实喜欢他的作品,拿过来就给他编,恐怕换了我们谁,身处卡佛那个位置,都没法拒绝编辑的好意,以及这种好意中包含的暴力。
1 \" U; v% G; X8 P g4 x
- A$ j& Z6 A2 d4 {7 l 我们见过无数愚蠢的编辑,拿过来给你瞎编瞎改,但是这个戈登·利什(《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编辑者)非常厉害非常强势,某种程度上讲,经他手确实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卡佛,而且他塑造的这个卡佛正好符合彼时彼地美国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口味和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戈登·利什不仅是卡佛的伯乐,甚至作为小说家的卡佛是卡佛与戈登·利什共同创造的。) q/ }( o' G7 M0 o& ^9 z6 _) W; e
$ v2 \( d, X, h, K/ h" f 这个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和文学生活,有的时候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甚至想,任何一个重要作家,包括伟大作家,都不仅仅像我们想的那样——我很厉害,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他很多时候是被各种力量参与塑造出来的,是被一个时代的各种力量,各种必然的、偶然的因素参与塑造,甚至有时候塑造着塑造着,作家自己都当真了,他真的被这种外力的塑造所影响,这也变成了他的自我塑造了。- P$ R, I# l& H/ g4 A
* L/ V. n3 T- p7 c0 T 卡佛在回忆录中老是说:我为什么是极简主义?其实我根本不是,我是没办法,两个孩子天天在那儿哭,闹腾得我受不了,我是没办法在这种哭喊中长篇大论的。其实他也没有极简,他也在啰嗦,但他渐渐地按照别人的预期对自我进行着想象和塑造。
) u; m, t) H2 j; h% b8 p- K* L
; m' Y" D, h8 v# A z* ` 酷就是直面现实吗# F; X- C; H/ o$ O0 `% U) I" g
+ {; [6 f' y7 H7 q" G0 K
我们现在从文本上谈卡佛,对原装的卡佛已经造成了不公正,因为我们有先入之见,我们一接触就是删减版的卡佛,我们是从删减版的定见出发来看现在的原装卡佛,在这个意义上说,原装卡佛已经吃亏了。* M7 W/ R& k- w& P1 o9 j
; |) O# N- H' L1 f. A B+ @2 x 戈登·利什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编辑,在这两本书中,我们看到他的很多删减是有道理的,是非常有力的,确实在有的时候把一个胖子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筋骨、体型非常好的人,这个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
4 ~+ l {, H! ~% e# \" E5 @3 w
6 I, C- k' _/ J; @8 O( [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话又反过来说,戈登·利什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很酷的卡佛,有时是袒露了人生的绝望和无望的卡佛,是一个充分展现了在这个冰冷世界中挣扎的卡佛,而原装的卡佛的酷度显然就没那么高了,或者说温度明显没那么低了。
* h- B* m+ X* v) q# g0 [3 b: R% l+ W7 K( w$ W: Q$ d
我觉得,这从根本上看不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还有一个作家的世界观问题。# k( l/ n8 _7 w) u) X+ j" f+ P
% D0 E5 q! w$ C" A8 g* Z9 W 比如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是一本极酷的小说,写了一个英国的地痞流氓,这本书在英国出版时是21章,最后一章,坏蛋从监狱里出来,成了一个有孩子的父亲,回归为普通人。
# o2 Q& ]: s, K) u7 c
; p5 }& Y I. K& ~2 z" ` 可到了美国,纽约的出版商大刀一挥,把第21章给删掉了,说不能这样,在美国人看来,这样搞很庸俗,充满了“性本善”的庸俗看法,要酷就要酷到底,要直面人生的黑暗,安东尼的第21章充分表明了英国人的平庸,只有美国人能够直面现实,而所谓直面现实,就是能够把这个酷一直酷到底。2 T# c' p, n- l5 h; K& j
* J6 j( v5 e" Y 对此,安东尼耿耿于怀,他在上世纪80年代写文章发牢骚说,美国人确实勇于面对现实,他们很快就在越南面对了现实。
& Q( ~, L8 M$ I0 v; {
* e; ]7 {6 k/ I6 B4 D4 t 该向卡佛学什么* t, ^; D0 M; c' ]1 j0 W
- Y! L- p2 X7 Z. K: [! p1 S! o3 |
安东尼对美国人的趣味表示不以为然,他说:问题不在于艺术上是否要那么极端,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对人生抱一个公正的看法。这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有意思。改装的卡佛能大获成功,因为编辑想“面对现实”,而未经改装的卡佛则坚持对人和生活表示公正看法。/ |& a7 w( S+ Q9 p1 n3 p7 [; j k
' f. p1 _& o1 ]; v* B8 y2 C% }
拿《新手》为例,虽然没有《谈爱》那么尖锐,像一颗石子、玻璃那么尖利,但是它对于人性的力量和看法可能更为宽容和公正,它让我们看到了绝望,看到了人生悬崖的尽头,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从那个悬崖上掉下去,更多的人在那个悬崖上给自己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倒觉得这个原装的卡佛是值得我们读的,也是有意思的。
( y6 X; M% I* b! D3 z6 H$ @7 Y' F
卡佛是一个命运多舛、命数奇特的作家,摆出两个卡佛让我们研究,让我们纠结,让我们站队和投票,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所有当编辑的人,都应该好好地把这两个版本比较一下,对于编辑能力、编辑权力的边界在哪里等问题,在这其中有非常好的例子。
8 o& O V' `( A; U+ U6 J V2 `$ k, U4 o5 m3 M1 u
两个不同的卡佛,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两种不同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戈登·利什的卡佛注定轰动世界,正如美国出版商把《发条橙》最后一章切掉后,安东尼·伯吉斯说这个绝对不行,出版商说你别跟我吵,切掉这个将轰动世界,但是安东尼·伯吉斯依然不赞成,依然不甘心,他依然坚持他所谓的对生活的公正态度。
N; ~5 r, o0 H: _+ b# N
) P! L/ F4 c2 F/ t9 P, W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甚至可以牵引出来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卡佛对中国作家影响深刻,但我们接受的到底是卡佛的哪一面?我们可能深刻地接受的是改装过的卡佛,那个卡佛对中国文学影响极为深刻,以至于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小说中不把事做绝,不把黑变成更黑,或者不把冰冷和绝望一推到底,就不算深刻,不算酷,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一个根本的艺术惯性和习惯了。8 T# H7 h+ h& C! R. X1 C% D1 E
3 ^4 p. `2 t8 U5 c9 b% h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来看新卡佛,从某种程度上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原装卡佛那种对生活的公正,包括对自己的忠诚,原装卡佛是个多么倒霉的人,但是他自己对生活始终没有那么绝望。某种程度上讲,他在坚持这种公正的时候,也是对自己的忠诚。
$ h9 _1 i! q9 }. H) P5 [8 h6 E8 W: V2 d) B H
中国编辑几乎放弃了编辑权- R7 l0 B( g- Q; E% q& t7 a
. Q8 b" W X3 T! U1 x0 P/ b$ P
中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编辑几乎完全放弃了编辑权,现在编辑哪有没事拿你的稿子改来改去的?哪有那个心思?这其实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事,在美国出一个长篇,编辑从第一页改到最后一页,要改得满天花。, u' W7 R. M; {7 Q$ O$ f4 v
; Z; ^3 m3 s3 |1 p3 d) D
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网络时代根本就不需要编辑,我写完了就贴,贴完了就转,全国人民就读,有编辑什么事?但我是这么看的,不管怎么样,五千年文化能传承下来,我相信还是要取决于一种精神的,比如写作,需要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像工匠那样,有一个非常投入的推敲过程,我想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我们的文化中缺少了推敲这两个字,可能到最后,我们就不会留下什么东西。& y1 | s6 \/ `6 O
& o8 g2 j( l/ |" X$ F- q4 I
! Y% r8 s) M2 h) s6 b9 l$ N8 {. o 我们制造无数的文字,但如果不做推敲这件事,那什么也留不下去。仅就推敲这件事来讲,不仅作家在推敲,编辑也在参与这个推敲过程,这个推敲过程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W1 t6 e- d( k; P1 |
) Q2 R) Y! z) O3 n: _& U- J& s 作家一定分好作家和不合格的作家,编辑也有大量不合格的编辑,他要给你推敲,能把你气死,他要给你改,能把你改死,但在好作家和好编辑之间,推敲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编辑和作家形成了一个张力,这个张力甚至不是为了说我要改变你这个作家,而是说能够使这个作家更好、更准确地发现自己、确立自己和塑造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和理想模式。
& U# I# u% d1 G6 t: h3 N5 o* Q P' ~: u! `& e" N1 N
我觉得这个时代依然需要好编辑,这样的好编辑确保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品质。我经常看书,看很多现代的小说,说实话,常常从专业上感到很生气,有的书如果能有个好编辑,完全能成为一本好书。在今天,很多作者比较放纵,对自己的文字不怎么负责,现在出书太容易,左一本右一本的,他不太负责,所以我始终觉得,维护时代的文化基本品质,还是需要有好的编辑和好的编辑精神。
% [/ K$ \$ G% r- Z0 W! R0 O* k
- T- \# U- `3 p p! u! E" I! g |
|